1992-1996年的中国大学正处于一个交界点。
彼时,大学还未大规模扩招,考大学依然不亚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。邓小平南方谈话带来了松动的气息,而毕业分配工作的“铁饭碗”制度却已悄然打破。新潮事物不断涌现,人的状态也耐人寻味。
在这种时代氛围下,1992年,当时还是大一新生的摄影师赵钢,背着一台相机走进了象牙塔。三百多个胶卷、上万张黑白底片,记录下了一代人的芳华。
如果说高考那一年是“蹲监狱”,那么上大学就是“刑满释放”。1992年夏天,经历又一个“黑色七月”之后,赵钢接到了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的录取通知书。
“那天,大客车沿着斯大林大街一路向南。一路上我心想:是不是快到了,是不是快到了。”直到接站的客车缓缓驶进校门,一个热气腾腾的新开端,终于扑面而至——
“欢迎新同学”的横幅标语、校园广播站的高音喇叭,以及手提肩扛着各式行李的师哥师姐们,全都热情得让人融化。
车窗外人头攒动,铺天盖地的指示牌一下子汇集到车门前。跨下中巴车那一刻,就像是人生每一个重要时刻的前夜,“好奇、兴奋,又有点紧张。”
1993年,一名新生脸上的表情正是此种心情的最佳注脚。
1992年,学费只是象征性的每年80元。相对应的,未扩招前的大学录取率也非常低,只有25%。1994年学费上涨后,围在窗口交学费的家长们往往要带大量现金,他们的表情里,同时闪现着喜悦和凝重。
1992年,军训还有打靶和持枪。1993年,打靶被取消,1994年以后,连步枪也不见了。
扛过神圣的军训蜕皮仪式,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“刑满释放”。至于释放后何去何从,这自古以来就是一门玄学。
“大学是过去意识形态桎梏的终结,是未来经济与人格自立的开启”。一个“终结”,一个“开启”,当中其实有着相当可观的操作空间。
——在突如其来的自由面前,一千个大学生,可以有一千零一种大学生活。
这种丰富性首先体现在课堂上。图为1994年,在书桌上象征性地放本书、在桌底下贪婪地阅读着书报的女同学。
上午的最后一节课,众饭缸子通常会带上吃饭的家什翘首企盼。
宿舍、食堂、教学楼三点一线之外,渴望生活的青年也急需一宽阔领地,将年轻的生活轰轰烈烈开展起来。
刚入学不多久,班主任便张罗了一场新生舞会,请来几位高年级的女生教跳舞。同学们大多羞涩,也有人很快掌握了技巧,迅速脱离了早恋有罪的苦海。
赵钢所在的摄影协会在宿舍布置了简易影棚,请来女生当模特,而背景布是一块白床单。
校运会上的啦啦队表演方阵,这是当时大学里能见到最性感的装束了。
92南巡讲话后,中国社会迅速升温,这种广袤无垠的激情,在大学的校园里更是蔚为壮观。
新潮一波接一波地来:录像厅热、气功热、古典音乐热、呼啦圈热、金庸热……作为社会最敏感的神经,大学生自然是时代的弄潮儿。
计算机中心里第一次接触电脑的94级新生。那时大家对计算机的学习热情特别高,不少人在课余时间额外花钱预购“机时”,练习上机操作。
下课后,“文学追星族”们将身一拧,投入到卧读武侠小说的旖旎中。而床板上贴着的张曼玉和钟楚红,也和金庸、古龙一起,成为少年梦幻之对象。
港台流行乐的风花雪月、台湾言情的滚滚红尘,无一不吸引着成千上万双渴望新奇的眼睛。90年代初,“麻派”、“毛派(指打毛活)”、“舞派”等生活方式亦颇有市场。
“打工”在90年代初也成了时髦词,彼时校方尤其鼓励贫困生勤工俭学、打工赚钱。
在代拿快递、代人上课这种校园业务还未如火如荼的年代里,众人搞创收的手法相当朴素:卖面条、发传单、承包洗衣机、挨个宿舍敲门兜售畅销书……
做家教则是最常见的“下海”方式。图为长春百货大楼附近的地下通道里,一名学生在安静地等待自己的“甲方”。
有人说,UNIVERSITY,不就是“由你玩四年”吗?但事实上,大学的生活,并非全然没有规则。
在你“无法无天”的头上,还悬着两把达摩克利斯之剑——“不被抓补考”、“必须过四级”。毕竟,90年代,文凭还是硬通货。
也有人紧锣密鼓酝酿着出国:“人活着,要有寄(GRE)托(托福)”,《托福600分单词》,就是他们的湖畔读物。
“启辉器占座法”是当时自习室的一大奇观:彼时教学楼里的荧光灯需要启辉器点亮,只要拿走启辉器,灯管就不会亮,底下的座位自然也没人座。于是有人专门带着启辉器去晚自习。
“晨跑卡”是学校用来约束学生早起的工具。每天早上6-7点,要把晨跑卡投到打卡袋里,为防有人代打卡,就连狂风暴雪天,学生会干部也会秉着“达康书记”般的责任感值岗。
军训期间,在摄影爱好者赵钢的招呼下,寝室七个兄弟拍下了第一张合照。后来有人看了这张照片说:“那时候年轻人脸上的表情和现在很不一样。”
事实上,“不一样”的,还有发生在宿舍里的故事。
在那个手机、电脑不知为何物的年代里,大家的娱乐总是集体进行的——尤其在“最强集散地”学生宿舍。
每天晚自习结束后到熄灯前的一个多小时,是宿舍的黄金时段。几乎每个寝室,都有不同的游戏轮番上演。“大家的脸都朝着同一个方向”,仪式感十分强。
锁上门、把消音用的毯子往桌上一铺,便可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过把麻将瘾。
“一三五打麻将,二四六看《渴望》”是当时的流行话,周末在宿舍集体追剧才是正经事。
在拳击的世界里,没有发泄不完的精力,只有打空了的对手。
总有些玩意会在宿舍里流行一阵子,呼啦圈、围棋、卡拉OK,1994年是乒乓球。
除了每天跑饭堂之外,酒精炉极大地改善了宿舍人民的生活。
饭饱后,再整上两瓶革命小酒,喝的通常是银瀑和金士百,那时候大家酒量都不错。
卧谈会是大学必修课。关灯后,随便揪住一个话题,聊家乡、聊经历、聊“今天在图书馆遇到的天使”……
直到哥们分期分批逐渐无声,最后一人才孤独睡去。
从1994年秋天起,学校开始实行男女分楼住宿。在理工科大学,女生公寓被男生称为“熊猫馆”,足见其世间罕有。
1996年,赵钢把照相机交给了女友丁凤园,于是“熊猫馆”的珍贵历史片段终于跃然纸上。
1997年,某女生宿舍里穿梭着动荡的笑声:有个女孩买了新衣服,大家轮流试穿。摄影 丁凤园
在同寝大三师姐们的影响下,97级新生章晓慧也学会了黄瓜美容法。摄影 丁凤园
1997年,403寝室的孟潘梅交了男朋友,男生买来甘蔗贿赂全寝室的女孩们。大家嚼着甘蔗,心中麻痒地讨论着感情里的小秘密。摄影 丁凤园
从大三开始,赵钢的镜头更多地关注起同学之间的关系,尤其是爱情这块被无数诗人讴歌过的圣地。
“你眉骨的轮廓太好看了……”钢铁直男的友谊也可以很细腻。
初中时,对女孩有好感会被定性为“早恋”;高中时,同学之间似乎也有某种默契:不谈感情。
高考结束那年,赵钢记得有同学暗暗发誓:“我上了大学,要先找个对象!”
一边是风度翩翩的弱冠少年,一边是穿着亚麻布裙子的白衣少女。在如同“化冻沼泽”般的青春期,荷尔蒙分泌起来,量大质优。而怀春的情愫正在集聚却未获名状,欲念浮动却不明就里——似乎总有一种朦胧,隔开彼此交投的视线。
在赵钢的印象中,89、90级的师哥师姐只是很安静地走在一起,就连当众牵手都不怎么好意思。在小花园的角落里,男生搂住女生的肩膀,就算是很亲密了。
清晨的小花园,阳光不燥,微风正好,女生们捧着书读得入神。
而1993年以后,大学中的情侣似乎越来越多,互动也越来越前卫——早上经过楼梯拐角,会听到读外语的声音,晚自习后经过,会听到情侣接吻的声音。
作为校园弱势群体的单身狗,则只能藏着花泽类式的忧郁,在操场边敞着被风吹开的领口,痴痴望着裹在黄昏里的恋人。
而对于赵钢来说,与女神相处,最好的打开方式就是邀她拍照。毕业那年,他也有了“俗不可耐的烦恼”。
1996年,一栋女生楼只有两部电话,而且只能接不能打,拨通的概率跟“秒杀”差不多。拨通以后,等待的过程同样揪心,首先听到的是宿管的声音:“找谁?”
1997年,赵钢回到学校,和还没毕业的丁凤园约会。再后来,丁凤园成了他的太太。
1993年7月初,89级离校的那天早上,赵钢在一间寝室门口,看到一名学长一动不动躺在床上——印象中,他们总是一副沉郁的样子——不久之后,这位学长就要发走行李,晚上坐火车离开长春。
1993年的那个早晨,是他在大学里最后一次躺在自己的床上。
四年时光打马而过,直到自己快毕业了,赵钢才明白个中滋味。那是一种无可明状的失落。
“上半身衬衣领带,下半身短裤拖鞋”,成为社会人儿之前,要拍一张漂亮的求职简历照。
90年代中后期,大锅饭和包分配的制度正逐步打破。1996年,大学毕业生就业已是双向选择。
从1994年开始,毕业生招聘会就越来越火爆。曾经的“时代宠儿”、“天之骄子”,面对汹涌澎湃的经济大潮,也有点茫茫然不知所措。
毕业那天,有同学买来一件白T恤请大家签名留念,正中央写着一句醒目的“今天应该很高兴”。
1996年7月6日这天,赵钢也在长春火车站,送走了自己的同学。
火车静静等在旁边,拉响汽笛前,人们站在月台上拼命挥手,无数双眼睛哭得丧失了焦点。“一边拍,一边流眼泪,其实早已看不清取景器。”
那天早上,室友刘道连在宿舍题了一首诗,赵钢用镜头将它永远记录了下来:
“学窗生涯今日休,岁月匆匆不可留。今朝别去空此楼,吾辈他年出风流。”
图片选自浙江摄影出版社《我的大学》
网易看客已获授权,转载请联系原作者
参考资料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[1]《我的大学》,赵钢
[2]《浮游在时代之上的大学生们》,阿铬
[3]《中国九十年代话语转型的深层问题》,王岳川
文章版权为网易看客栏目所有,
公众号后台回复【转载】查看相关规范。
看客长期招募合作摄影师、线上作者,
后台回复关键词即可查看。
看客
 扫一扫下载订阅号助手,用手机发文章
赞赏
扫一扫下载订阅号助手,用手机发文章
赞赏
长按二维码向我转账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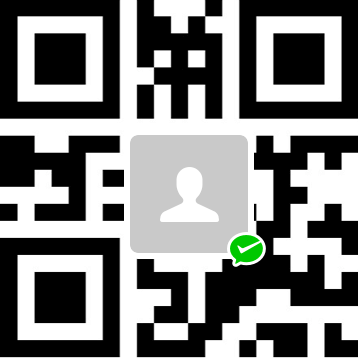
受苹果公司新规定影响,微信 iOS 版的赞赏功能被关闭,可通过二维码转账支持公众号。
朋友会在“发现-看一看”看到你“在看”的内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