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9年3月30日18时许,四川省凉山州木里县境内发生森林火灾。
31日下午,四川森林消防总队凉山州支队指战员和地方扑火队员共689人在海拔4000多米的原始森林展开扑救。受瞬间风力风向突变影响,扑火人员在转场途中突遇山火爆燃,27名森林消防指战员和3名地方扑火人员失联。
目前,30具遗体已全部找到。应急管理部工作组已到达现场指导开展搜救、善后及灭火等工作。
前往现场的,还有摄影师程雪力。
作为一名鏖战山火12年的资深消防员,他时常与原始森林打交道。十多年间,他走过最偏远的大兴安岭腹地,最艰苦的世界屋脊青藏高原,共扑救过124场森林火灾。
以下,是他所经历过的故事。
水火无情早已是无需证明的定论。至于在森林里打火,则是一种让人感受更复杂的工作。
它既能让你有活着的感觉,也能让你随时丧命。
19岁那年,我的身份由“学生”变成了“扑火的兵”。作为新兵蛋子,彼时的我还不太明白,美丽的雪山和原始的森林是怎样的天堂,也不太明白,大火肆虐时它又是怎样的地狱。
只知道山里每个区域的小气候总是变化多端,水汽凝结成大雨滴,噼噼啪啪,每棵植物都在下着自己的雨。
四个月后,我遇到了人生的第一场大火。
这场火起源于四川西昌的森林。我们沿火线向东侧推进了3公里时,大火在7级乱风的作用下以交叉立体的姿势燃烧,瞬间形成了一百多米高的树冠火。
漆黑的浓烟笼罩在空中,明明是白昼,却昏暗如黑夜。黑灰色的流云中穿过几只叫声极大的乌鸦,远处传来类似爆炸的声音,身边不时有大树倒下。
此情此景,和欧美灾难片里的世界末日别无二致。据说当时空气里的有害物质,是北京雾霾最严重时的数十倍。
我被吓得不知所措,像一只无头苍蝇到处乱撞。慌乱中我听到了老兵的怒吼:“一直往下跑!”我们迅速撤至500米外。
比明火包围更可怕的,是在几公里以外的火势。你看不见火势有多大,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从什么方向袭来,只有燃烧的声音像嘶吼一样要将人吞噬。
整片森林从中心喷发出灼人的气浪,而另一个山头的森林不到一分钟就烧没了。
这场火最终打了几个昼夜才扑灭,肖兵和赵国涛一直冲在最前,他们的灭火机一直到最后都好使。
这一年,我们一起打了10多场大火。每次打火回来,李俊超抽起烟来都觉得无比轻松,感觉自己卸下了一个包袱。
2017年,内蒙古大兴安岭,一棵在特大森林火灾中幸存的白桦树。
2011年在四川冕宁,我的战友杜鹏飞告诉我,当时如果不是后方战友打开突破口,他们很可能会搭上性命。
当时他和另一位战友白章亚在半山腰灭火,风力突然增大,燃烧的倒木纷纷往下滚,他们周围瞬间出现了两个新的火线。火势迅速向山上蔓延,浓烟四起,在被重重围困的绝望中。直到负责火场东线的二排为他们打开了撤退的突破口,他们才得以逃脱。
2014年4月,四川西昌市开元乡发生森林火灾,战友王帅需要背着20多斤的装备攀爬悬崖。突然他脚下一滑,眼看要掉下山崖。就在一瞬间,他抓住了一根并不粗的树枝,其他战友迅即用攀登绳把他拉了上来。
那一刻我觉得,我们救护着森林,保护着战友,森林也在秘而不宣地保护着我们。
从汶川地震灾区回来的第二年,我花了4个月的津贴买了一台“傻瓜机”。
灭火机的油门一如既往地加到最大,而我开始将镜头对准这群出生入死的森林消防员们。
以前,我总想象不到天堂和地狱的样子。但每当我看到被烧死的森林,头脑中便出现了2016年在大兴安岭看到的森林雪原。
头脑中,也就有了“天堂”与“地狱”的印象。
那是2016年冬天,我前往北纬52度的内蒙古大兴安岭北部原始森林腹地,拍摄奇乾中队的故事,他们驻守着中国唯一一片集中连片、尚未开发的原始森林。
这里被外界称为与世隔绝的“林海孤岛”,一年中有6个多月大雪封山,偶尔零下50℃,不通邮政、没有网络、没有市电。
营区如同硕大蚕茧中的一只小蛹,被层层叠叠地森林包裹着。举目望去,是碧蓝的天空,和无穷的原始森林。
在来奇乾中队之前,我带上了我认为最重要的防寒物资,包括心理上的准备。
可是落地以后,我依然被冻得有些木讷,就连相机说明书上也显示:不要在零下25度以下使用相机。
但战友们的热情让我内心化雪,就连中队那几条狗,也用最高的礼节招待我们。“呆子”一嘴咬到温柏志的胳膊上,轻轻地打了个招呼以示欢迎,但第二天他就下山打疫苗了。
实际上,部队里的警犬都有战斗编制,执行着特殊任务。
我在这里住了10天,本来想拍摄他们在深山老林里如何枯燥乏味,如何不易,如何坚守。但越是深入,便越是发现,奇乾战友的生活不需要煽情,他们的幸福指数其实比我还高几倍。
魏征告诉我,有一次他从外面取水回来后,裤子被冻硬了能立起来,自己看到都想笑。
只要进入冬季,河流停止了喧嚣,他们就能在上面踢球。
有人说,在奇乾,没有伤病就是幸福,有了伤病、能够及时得到医疗也是幸福——虽然,单从照片上看,他们确实像生活在月球上一样……
奇乾中队的平均年龄只有23岁,百分之九十是90后。
当兵前两年,胡彭冲都没有下过山,也没见过一个女孩。前些年想念家人的时候,就爬到后山上找信号,有时能断断续续地找到一格。
这里的信号微弱得伸手就能挡住。大家伙又想办法,把手机挂在树上,先把电话拨出去、打开免提,然后站在树下面扯着嗓子喊话。因为人人都操着自家的方言,于是那情景便有点像大合唱里的N重奏。
这种方式一直持续到2015年8月份,信号问题基本解决了,但网络对于胡彭冲来说,还只是一个外星概念。
回家休假时,胡彭冲和相亲的姑娘相互有好感。姑娘想加个微信,他才下载了微信客户端。那时,胡彭冲的微信里只有那个女孩,女孩也是他对“微信”的唯一概念,但一回到单位,又没有了网络。
2017年春节,许多奇乾的战友加我微信,兴奋地告诉我他们通4G网络了,第一件事就是和我视频。
面对眼前这95万公顷的森林,奇乾中队50多名巡防官兵的人均防火面积,约为24000个标准足球场大小。
但面对天灾人祸,没有哪种准备说得上充足。
中国的土地上,平均每年要发生1万多起森林火灾,一片被烧毁的森林,往往需要20年甚至更久才能自我修复。
我不知道,这些冰冷的数字对于人类而言到底是何种意义,也不知道眼前的景色何时会一夜坍塌。唯一能确定的是,12年间遇到的124场大火并未将我塑造成更勇敢的人。
相反,我感受到的是人的渺小。一片森林从繁茂到消失,又是多么脆弱易碎。
从白昼到黑夜,从绿光到火光;从春夏到秋冬,从服役到退伍……这就是我经验着的“另一个世界”。
常年在大山中行走,我的语言和思维已经跟不上时代,比起“天堂”和“地狱”,我更向往“人间”。每次打火回来,穿行在皑皑白雪中,心里唯一向往着的是一顿热饭,还有一张温暖的眠床。
然而,此次葬身于火海中的30名森林消防员,却再无机会看一看这“人间”。
文章版权为网易看客栏目所有,
公众号后台回复【转载】查看相关规范。
看客长期招募合作摄影师、线上作者,
后台回复关键词即可查看。
看客
 扫一扫下载订阅号助手,用手机发文章
赞赏
扫一扫下载订阅号助手,用手机发文章
赞赏
长按二维码向我转账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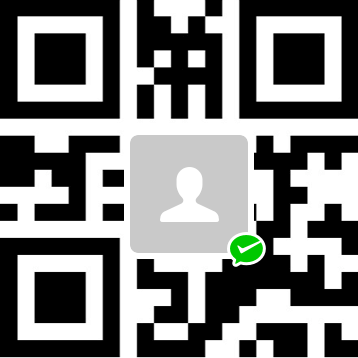
受苹果公司新规定影响,微信 iOS 版的赞赏功能被关闭,可通过二维码转账支持公众号。
朋友会在“发现-看一看”看到你“在看”的内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