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在北疆的秋天,发了一个长长的呆  在这里,撞见最美的风景。 同样在天气微凉的九月,90后女孩宝妹揣着相机,前往乌鲁木齐。
那是北疆一年中最美的季节,湛蓝的天空万里无云,底下是淡淡的鹅黄色房子,风景如油画般温润。
不做攻略,见机行事,宝妹在辽阔的北疆呆了二十五天。
她从城市走到村庄,再只身前往大山深处的幽静小镇,然后发现自己所期待的诗与远方,不过另一些人的琐碎日常。  山里的老爷爷为宝妹摘下一朵花。 “每一个人身上都拖着一个世界,由他所见过、爱过的一切所组成的世界,即使他看起来是在另外一个不同的世界里旅行、生活,他仍然不停地回到他身上所拖带着的那个世界去。”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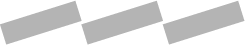 抵达乌鲁木齐的那一个星期都是好天气。
由于跟北京有两小时的“时差”,白日仿佛被拉得很长,到了夜晚八九点,天色仍亮。
我每天睡到自然醒,拿着相机在街头行走,总有时光错乱的感觉。  小孩踏过工地的尘土。 乌市的城市建设和许多大城市一样,有拔地而起的高楼,炫目的霓虹灯,地铁也将开通(我离开两个月后就开通了)。
不过,我从未在任何一个都市的街头,看到如此优雅的行人。
女士们总是裹着精致的头巾,脚踩低跟皮鞋,哪怕只是为了出门买菜。  一位从超市走出来的老太太。  提着馕的女士,仿佛提着一款时髦的名牌包。 老爷子个个穿着体面的西服和皮鞋,头戴小帽,三三两两坐在长凳上聊天。  一位笑盈盈的老爷爷,他的眼睛有光。 朋友告诉我,时间往前倒十来年,乌鲁木齐还没有现在这么繁华。
那些漫长的夜晚,人们在空旷的场地上跳舞,在电影院门前约会,到街巷里吃烤肉,嘴里哼着歌谣。
即便处于现代化过程中,老人身上还是散发出一种近乎古典的韵味。那些日新月异的新鲜事物就像来自海洋的温润气候,难以到达这座远离海岸线的城市。  即便套着环卫工作服,里头依然是精致的裙装。 离开城市,村庄则是另一番模样。
我去了号称“中国最美乡村”的禾木村,那正是禾木村最美的时候,但也是游人最多的时候。
游客们五颜六色的冲锋衣、墨镜、防晒帽,比金黄的树叶还要抢眼。
村里的小木屋都被改造成了客栈,青旅床位最低也要100元/个 —— 这是我在国内睡过最贵的床位。  在禾木村里,我发现了中国最酷的兰州拉面馆。 和旅社老板聊天时,他给指了指远处的一处山峰,“那就是美丽峰,山上有大概七八户牧民,他们有专门的床位,给游客留夜。”
于是我决定避开熙攘的人群。
经过了三个小时的徒步,山上的一切像童话般在我眼前展开 —— 大片大片的金黄,图瓦人的原木尖顶小木屋、牲口围栏随意散落在村子各个角落。
我在院子里看到一个骑自行车的小朋友,毫不犹豫走近,跟他打了声招呼。顺理成章住进他们家,独享一间小木屋。  阿扎玛提在自家荡秋千。 男孩叫阿扎玛提,是房主夫妇的孩子。
房主白天带着马匹下山拉客人,他太太在山上经营着青旅一样的小木屋,给客人提供食宿。
整个山上,就只有七八户人家。
早上,我和一家三口在一张桌子上吃早饭。阿扎玛提跑前跑后,给妈妈帮忙。
一直很害羞的他突然问我,要不要再加一碗?
当然要。我们就这样熟络起来。  我的早餐,奶茶要大碗大碗地喝才带感。 阿扎玛提第一次告诉我他名字的时候,我没记住。
后来有人告诉我,Azamat 在哈萨克语里的意思是:英雄。
阿扎玛提觉得拍照是件很酷的事情。
他拍自己,拍小伙伴,拍草原上的狗。还问我,“可以给你也拍一张照吗?”  阿扎玛提问我:“怎么一个人跑来这么远的地方,你的朋友呢?”
我说:“你就是我的朋友呀。”
他低下头,有点害羞。
奇妙的是,2019年8月,我的一个朋友也去到禾木村,居然偶遇并认出了阿扎马提。
时隔一年,男孩长高了,更健壮了。他还记得我,对着手机和我说,“好久不见”。
然后腼腆地钻进朋友的怀里,只剩下山顶的风呼啸吹过。  猪鼻子。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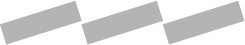 禾木玩得差不多的时候,朋友发来消息说,如果时间宽裕,可以去他伊犁的家住下来,慢慢玩。
他快两年没回去了,但家里的老爷子老太太都在。
于是我坐了快8小时的小巴士,一路颠簸,抵达大山里的尼勒克蜜蜂小镇。  老太太和老爷子在家门口合影。 两人住在山脚,有一间种满了花果木的大院子。红艳的小草莓入口即化,枝头的青苹果熟透了,一颗一颗往下掉。
小镇的生活,就是在苹果树的结果和凋败中,在太阳升起又落下的循环中,平稳地前进。
太阳好的时候,我就坐在院子里晒太阳,读着王小波写给李银河的信,从十点到一点,偶尔大声读给老太太听。
院子里的风尘越吹越大,老太太随手拿了她的大帽子盖在我头上。
坐久了,我带着困意回屋,床上铺满一被子的阳光。  老爷子每天很早就醒来,给院里的菜浇浇水,看看蜜蜂,下午找朋友们聊天。
他告诉我,他在这里养蜂产蜜五十年了。
“哇,五、五十年啊?”我一脸惊讶。
“是呀,那时候我才十七岁咧。”  老爷子在院子里播撒种子。 老爷子的老家在江苏,17岁就搬进了新疆山里。
我问他会不会想念故乡,老爷子回答:“是有搬回去过一次,到城市里。他们天没亮就起床去上班,在集市里,为一两斤的东西讨还几毛几分的价。”
“在新疆山里,我睡到自然醒,很晚才起来劳作,赶集是好几公斤地交易,酒大口大口地喝。”
“在江苏呆了3个月吧,我就又下决心搬回了新疆。”  老爷子坐在客厅沙发上,边看着电视就睡着了。 不呆在家里的时候,老爷子喜欢爬山。山不高,半小时就可以走个来回。
他走得快,我在身后跟着,拍照,偶尔搭个话。
如果我落得太远,老爷子也不做声,只是停下来等我。  爬山途中,我对山上的几头牛产生了兴趣,老爷爷便坐在树下等我。 我和老爷爷的相处,就像两棵树,各自笔直,在风声中相互致意。
他带我爬山的时候,我就静静地跟在他身后;他在客厅看抗日剧场的时候,我就坐在他身边静静地看;他在院子里播撒种子的时候,我就静静地给他拍照。
不知道为什么,拍下这些照片时,我总是想起《一个人的朝圣》的主角哈罗德。
在七零八落的瞬间里,建立生活的仪式感。  相比之下,我和老奶奶则亲热得多。
散步时,她会牵起我的手;听到我喜欢吃羊肉,她第二天就炖了新鲜的羊肉汤;当邻居问起身边的小姑娘是谁的时候,她会开玩笑说,“这是我的女儿啊。”  老太太笑着给我比了个耶。 老爷子和老太太都是汉族人,尽管住在这座北疆小镇,他们的日子似乎和我老家村子里的老人们并无太大差别。
直到他们带我参加了一场哈萨克族的宴会,小镇居民们的真实生活,才在我心里立体起来。  一位美丽的大姐在为派对上的客人准备食物和热奶茶。  七零八落的皮鞋。 那是位哈萨克族小朋友的生日。按照他们的传统,要宴请友人,歌舞欢庆。
派对上,哈萨克族朋友个个盛装出席,见面时热情地拥抱亲吻。
麦克风和音响已架在院子里,搭配着旋转的舞灯,像露天的KTV。
老爷子说,“他们可是要唱跳到天亮的!”
我们三个汉人,穿着羽绒服,再用围巾把脖子裹得严实,但还是冻得不行,八点过后就离开了。 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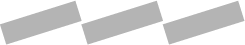 就这样,我在北疆的秋天里发了一个很长的呆。
直到旅程快结束的时候,我突然好想去看一看雪。
看雪要去百公里外的山,一贯晕车的老太太坚持要陪我去。
她告诉我,之前曾有人这样陪她去看雪,所以她也要让我看,让我开开心心地回去。
于是我们租了车,一路开上山。   我在山上留下的自拍。 在北疆的25天,像风一样扑过,然后远去。幸好我还有许多照片。
回到上海的时候,两位老人会偶尔给我发微信:
宝妹,祝你生好运,我们倆口盼你,再回来我们这玩。我们盼你,孩子。
看到这句话时,我仿佛闻到了老太太枕头的艾草味,沉凉而稳妥。
仿佛依旧身处清秋的北疆,身处老爷子的院子里,那拥抱坠落苹果的草地上。 摄影 宝妹 | 采写 东北旺 | 编辑 小胡 JR 每周一三五 晚九点更新 文章版权为网易看客栏目所有, 公众号后台回复【转载】查看相关规范。 你可能还喜欢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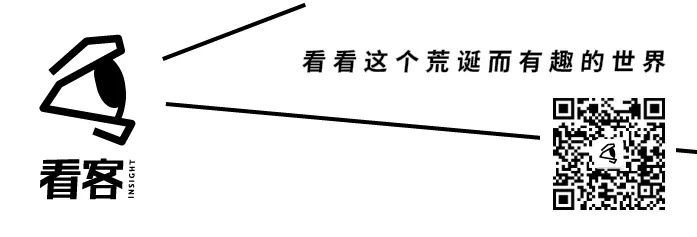 看客长期招募合作摄影师、线上作者, 后台回复关键词即可查看。  |
朋友会在“发现-看一看”看到你“在看”的内容